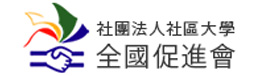一
社大十年。
從1998年第一所社區大學在文山成立以來,社大運動走了十年,一路真是跌跌撞撞。
在資源與空間極其有限、社會支持度相對薄弱、穩定度欠缺,而主流價值對社大的認知與社大本身的自我定位之間,又有巨大落差的情況下,社大能從這夾縫裡抽芽、成長,真是台灣社會的奇蹟。
這奇蹟是靠無數對社會改造抱著無限熱情的朋友們,在各個角落堅守崗位,為理想注入心力,共同開創出來的。尤其第一線的朋友們更是辛勤工作,耗盡心力,日夜在剝削自己。我只是早期倡議社大運動的一員,沒有資格出面來感謝這些朋友們的默默付出,但台灣社會應該深深感謝他們多年來辛苦的耕耘。
十年社大。今天應該討論的主題是社大的存活、深化與種種現實的問題。可是我從2001年春天就從第一線退下來,對實務已相當陌生。幸好顧忠華教授及其他同仁,在接下來幾個場次都會與大家深入討論這些重要而實際的議題。顧教授的引言文〈社大的發展策略〉中提出許多很好的策略,像設立「台灣社區聯合大學系統」、「成人教育進修學院」或「與空大合作」等等,希望大家能認真考慮,形成共識。周聖心談〈學分學位的認證與接軌〉,也很實際可行。
另外,我剛剛特別提到社大的存活,是因為有些縣市政府用「最低標」的競標方式,決定縣市內社大的承辦或續辦。這是反淘汰的作法,優質的社大可能因此被劣質的社團或財團法人取代。這是嚴重而且急迫的問題,我們也應該藉由今天「社大十年」的研討會,向社會發聲,要求這些縣市政府改弦更張,用「評鑑」或「最有利標」的方式,來委辦社大。
讓我把社大往後的實務問題,留給以後的場次討論。現在這個場次,我將集中重談談社大的定位。
1998年文山與青草湖兩所社大相繼成立。同時,台北縣五所社大在當時的縣長蘇貞昌先生的支持下,也開始籌備。我在台北縣設置社大的評議委員會上說:
「社區大學是台灣社會的新生事物。」
當場有些回應,但對「新生事物」這個概念,只停留於各自表述。
為什麼說是「新生事物」?新生事物指的是:「從沒有出現過的東西」。任何東西從無到有,當然都是新生事物。一家麵店在某個街角開張,本來這個街角沒有這家麵店,現在這家麵店開張了,它便是新生事物。我的意思當然不是這樣。我談的是內容。如果這家店賣的,是從來沒有人賣過的東西,而且這家店營業的立足精神都與過去的店大相逕庭,那麼才說它是新生事物。
社區大學賣的兩樣東西:「知識解放」與「公民社會」,都是台灣社會從來沒有有開展過的東西;而社區大學本身,便是公民社會的一個樣態,這個樣態既跳脫集體意識,也不自囿於唯心主義,所以它對於台灣社會,也是陌生的。台灣社會到處都可以看到集體主義的影子,也到處都可以聞到唯心主義的氣味。超越集體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成人學校,對台灣社會,自然也是「新生事物」。
因為這個緣故,我說社區大學是新生事物。
二
社大成立之初,大家有個共識,認為社大的定位在於「尋求知識解放」與「催生公民社會」。十年過去,我們要重新檢視這兩個主要目標在社大發展中的位置。
關於「知識解放」,我在1999年寫過的一篇〈經驗知識與套裝知識〉,已大略勾畫出它的意義。並提出以(1)問題中心;(2)經驗穿透;(3)切入根本問題的入手方法,來發展經驗知識。十年過去,知識解放不易開展的原因,主要是外部條件不夠,例如沒有學位的誘因、修課學員的人數不足,導致許多學術課程無法存續。(而且當修課學員的動機,沒有強烈到願意為所修的課程,投入足夠多的心力,很多功課沒辦法要求學員花時間完成,這在一些自然科學的課堂上,學習效果會大打折扣。)沒有長期的實踐,便無法持續發展。
在一些成功開授的學術課程中,許多講師都不斷在嘗試不同的方法,得到很好的成就。但有些核心的工作人員不斷反應,要找到能掌握社大精神的師資不易,而且以目前這種方式開授學術課程,要進一步連結到個人世界觀的重建,更是困難。當然,十年來也零星出現過一些成功的個案。
十年來,社大有許多朋友都為知識解放如何落實而殫思竭慮,提出種種想法,有些甚至進一步著手發展社大的特有課程,例如社大核心課程的設立、成人教育知識論的研究、三類課程的整併、「與世界連結」系列課程的發展與藝能師資工作坊的推展。這些現象,讓人看到社大內部充沛的生命力,尤其是它不斷反省、不斷修正、不斷創新的活力。
對於這些努力,我有幾點補充,也許有助於知識解放的實踐:
- 一般人想到知識解放,便立即想到要把學院的專業知識經驗化,轉譯成淺顯易懂的白話。這當然不容易,要做好它,必須先找到精通本身專業又有能力轉譯的人,投入心力來教課及編寫教材。如果能找到並集合這些人才來做最好,核心課程也許可以在這樣的基礎之上,結合網路的資源,像OpenUniversity的教材、MIT的開放課程等等,慢慢規劃出來。
但這些需要許多條件與時日。事實上,我也零星的看到有一些兼具專業與轉譯能力的講師,正在開授這樣的課程。
對我來說,在現有的限制之下,如果願意退求其次,改從課程規劃者的立場,轉向學習者,針對學習者的主體性,重新看待這個問題,事情也許還有點樂觀。
- 我思考「教育」的問題,通常會不斷回去檢視自己的成長歷程,回去探究周遭親人、朋友們的學習經驗。我相信大部分人最有效而紮實的學習,都不是靠聽教師講課而來,而是先靠「點」的啟發。這裡所說的「點」,是讓你忽然觸電似的概念、衝突、故事、畫、音樂或某種特殊的感悟。例如「基因變異」、「時空的相對性」、「開發主義」、「階級革命」、「邊緣化」….「拿破崙進入莫斯科空城」的故事…。然後藉一本書、一些資料,你開始把一些相關的「點」連成「線」,變成較有系統的知識,進一步你透過觀察、思考、閱讀、討論、體驗再觸類旁通,把「線」拓開成「面」。這樣學來的知識,才會黏附於你的生命,變成你自己的一部份,變成別人拿不走的東西,也才會促發人的知性成熟。
- 這便是我所說的「知識經驗化」。學習者是個主體,是他自己把知識經驗化,這些知識才會變成他主體經驗的一部份。別人(包括教師)是無法代替他,把知識經驗化。如果你同意我所說的這種「點—線—面」的學習觀點,那麼社大要做的「知識解放」將變得容易而有效。課堂上所能做而且該做的,便是「點」的啟發,然後提供共同閱聽與思辨討論的場域,催化人自己去連成線,至於最後能不能延伸到面,就看個人的造化了。
- 這裡我漏掉一個重要的東西:「抽象能力」。人可以靠閱聽與討論,幫忙他從點走向線與面,但最後最紮實的方法,還是要依靠自己的抽象能力去做系統化的連「線」,進一步去整合經驗、觸類旁通,拓展成「面」。抽象能力是太早失學的成人比較欠缺的能力,因此社大學術課程若容許三成的套裝知識課程,催化人的抽象能力,不見得不好。
- 無論如何,從「點」連成「線」與「面」的能力,難免要看個人的造化,但透過資料與故事,共讀與討論,每一個人還是會學到很多東西。用這樣的學習觀點,重新看待社大知識解放的工作,就不會那麼沈重而遙不可及。每次談到通識教育,談到知性教育或獨立思考,大家就會露出苦瓜臉,因為有學問又通達人世的師資難求,而且精心規劃的好課程也非常難得。但是從學習者的主體性來說,「大師澤被」或「精心調教」,未必是福氣。
- 自然科學的課程,就自然觀察、生態保育、永續發展這些方面的師資,比較齊備,而且已現存於台灣各地。至於物理、化學、生化方面的專業,人才只集中在少數大學附近,況且他們也不一定擅於轉譯成經驗知識。可以考慮共讀一些科普書籍(輔以網路資源如MIT的開放課程),等社大有了學位之後,再進一步發展。
- 在人文與社會方面,除了現有一些已經帶得不錯的課程之外,不妨考慮共讀重要的小說、報導文學與歷史事實的書。諸如讀托爾斯泰的《戰爭與和平》、《安娜‧卡列妮娜》以及羅曼羅蘭《托爾斯泰評傳》,便有許多「點」的啟發,也有無數可供連成「線」與「面」的討論資料。
- 研究成人教育的知識論,當然不錯,只是我擔心沒有那麼多的內容可以探究,除非引入腦神經認知科學,從事尖端研究,可是這類研究又非社大可以提供。建立成人教育的知識論,先要問幾個根本問題。為了答覆這些根本問題,去進行研究、建立理論,研究才會有生命力。不為結構化而結構化,這是我長年的看法。課程結構化的想法亦然。有些時候,我覺得某些教育理論,不太需要耗費心力去做。社大年輕有創造力的師資,行有餘力應該直接切入台灣社會與文化的研究。讓我引述1999年我在〈幾個問題,一個夢〉文章中所寫過的一段話:
如果社區大學中有年輕又具才華的師資,能把社區大學當作發展另類學術與文化的搖籃,珍視大家交會與激盪的時刻,深入耕耘,深入研究,也許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,會有某一個社區大學,變成一流的大學,就像紐約前身為社區學院的NewSchool,如今已成為社會科學的國際重鎮。最近我讀吳潛誠寫的《航向愛爾蘭》一書,書中談到愛爾蘭文學在喬哀思與葉慈等人的手中,如何從蓋爾特(Celtic)古老文化中汲取養分,建立新傳統與新文化。社區大學若人文薈萃,有朝一日或許會從平地建立起台灣的主體文化。勾繪這些願景,就當它是作夢吧,談這些無非是想讓年輕人用另一種心情,認真的來經營社區大學,也經營自己。
(9)社大是有條件把研究的主力,與一般大學技術性的研究做區隔,放在大格局的、有生命力的學問上。這是更上一層的知識解放。
三、
什麼是「公民社會」?公民社會的特徵是:公民經由討論、學習及參與,可以影響甚至主導社會的公共政策,可以塑造自己周遭的公共環境,累積起來會展現社會多元活潑的新文化,並形成國家的新面貌。
例如:社區或一村一里的公共建設,像道路的闢建與拓寬,或地方的設廠、土地開發、河川加蓋等,有無機會開放居民參與討論、共同規劃,才作成決策?再例如居民覺察河川污染、林木砍伐、公用土地被侵占,或周遭的生態環境遭到破壞,社會有無機制迅速回應,並加以處理?又例如公共資源的分配、知識與技能的學習,有多少管道開放居民集思廣益?
社區大學標舉的「公民社會」,並不是什麼艱深的學理概念,而是社會具體的生活情境。近幾年政府及政黨大量在變賣公有土地,轉手讓渡給私人或財團,人民全無置喙的餘地,這便反映了台灣雖然已經擁有高度的言論自由,廁身民主國家之列,但這樣的民主只是選舉民主,距離公民社會的理想還非常遙遠。舉個例子,以台北首善之地,捷運逐一完成,市容也逐漸改善,公共空間是形成市民新文化最重要的場所,像新店捷運站是新店-淡水線的終點,又在碧潭河畔,為風景勝地。原本捷運站前有一大片廣場,若能提供市民發展文化活動,像即興表演、音樂、舞蹈、戲劇,或弄跳蚤市場、有機農產品市集,將蔚為一大景觀,可惜捷運局在未告知市民之前,便把廣場變賣給建商蓋大樓。此事只有少數居民起而抗議,但木已成舟,徒呼奈何;多數市民也默默承受,不聞不問。
再舉些例子,都市街道的規劃純為便利汽車。行人與單車在都市裡幾乎無路可走,多數市民出門走路,都備受汽機車的排擠與威脅,可是幾十年來大家都默默承受,發不出聲音。
最近容積率的限制被大幅放寬,一時雖有利於地主及房地產業者,但長遠看來勢必嚴重衝擊城鄉居住品質,而且江河日下,以後再難回轉。人民大眾手中雖然握有選票,但也只能默默承受,或冷漠以對。
人民對自己工作與家庭以外的事,對自己生活周遭的公共環境,對文化教育社會福利的政策,在制度上沒有發言權,任由自己的利益受損或公共環境惡化,卻只能默默承受或冷漠以對。這便說明了台灣社會的選舉民主,距離公民社會還有很遠的路要走。
四、
催生公民社會,有兩個層次的任務:
- 促發公共意識的覺醒
- 在實踐面上發展公共力量
本來社區大學屬於社會學習系統,任務應以第一層次促發公共意識為主,但十年來許多社大透過實作,直接參與公共事務,也進入第二層次在實踐面上發展公共力量。由南而北、由東而西,都可以看到台灣社會這股新生事物的力量,從台東南島社大致力部落文化、宜蘭社大深化社區營造、建立地方學、旗山美濃社大發展城鄉交流、高高屏社大深研地方文史、台南社大從事河川巡狩、二仁溪整治、拯救樹蛙、北門社大進行海岸監測、…,這些成就在在引人側目。
從公共參與的實踐,促發公共意識,這是最有效的做法。各社大能為公民社會的理想,先「起而行」後「坐而言」,是台灣各級教育沒有的現象。
另一方面,社區大學生活藝能的課程,將會為未來公民社會的新文化鋪路。藝術課程透過繪畫、舞蹈、戲劇等,深入個人的內心世界,釋放情感,並使人對內對外的感覺更加敏銳而細緻;技能課程則實用而有趣,引人投入,像木工、水電、裁縫、餐飲,讓人從動手做,享受創造結合生活的樂趣,從而回歸自身存在的價值。這種種來自生活多樣的文化,一方面充實了個人的生活內容,另一方面,也將形成未來公民社會的新文化。
五、
社大十年,最耀眼的成就,便是催生公民社會這件事。
當然,這些努力距離公民社會的實現,還有遙遠的路要走,根本的癥結在握有政治權力的人,仍然沈迷於政治遊戲。我在前文〈倡議社區大學的初衷〉(引言稿之一)用很多篇幅談台灣政治的背景,是因公民社會與政治息息相關。對我來說,政治便是國家權力與資源的分配,公民社會不能只靠少數人的「觀念」與「決心」,便能達成。如果權力與資源沒有下放,只靠少數人的努力,很難打開局面使公共參與變成制度,進而發展出公共力量。
在〈倡〉文中,我提到目前台灣主要政黨都是右派:民進黨中間偏右,國民黨是右派混合極右。公民社會的思想在政治光譜上則為中間偏左,它的落點在主流之外。社區大學既要催生公民社會,當然是台灣社會的新生事物。就因為是新生事物,所以社大的存在,對台灣社會極其難能可貴。
但反過來,由於兩大黨的政治光譜偏右,而且進一步往右傾斜的趨勢銳不可當,社大若要繼續堅持「公民社會」的理想,必須凝聚更多的智慧,儲備更強的決心。公民社會必須建立在人民的主體性,這個原則不能鬆懈。最近在千里步道運動,我寫了一篇文章〈在藍綠的對抗中,談人民的主體性〉,試圖說明人民在政治勢力的夾縫中,必須堅持就事論事的原則,帶領政治人物的行為趨向公共利益,而非因怕介入政治,反而被政治勢力牽著鼻子走。
公民社會的特徵是對公共事務,就事論事。誰,不管是藍是綠,所做的事,如果符合公共利益,人民便公開讚揚,如果違背公共利益,人民便公開批評。
不能假裝中立,不能投鼠忌器。這個原則沒有確立,人民就會被政治人物或媒體操弄。只有就事論事,這樣人民才能變成真正的頭家,才能帶領引政治人物的行為趨向公共利益。
老實說,八十所社區大學如果能夠凝聚在一起,相互奧援,經常透過密集討論,就事論事,對公共政策形成共識,向社會公開發聲,社大將成為台灣社會一股清新的、重要的、代表公共利益的正面力量。
這股正面力量,反過來會回饋社大,幫忙打開社大本身的發展空間,不致讓社大凡事必須忍辱負重,而且這股正面力量本身,便在催生公民社會。
當然,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卻是處在今日政治勢力的夾縫中,社大要催生公民社會的理想,不能不認真考慮的作為。
倒是「知識解放」這個目標,我遠較樂觀。只要社大能取得法制地位,可以頒授學位,學術課程便能穩定發展。倘若國內認同度不足,不妨趁全球化之便,與國外大學合作。顧忠華教授倡設「台灣社區聯合大學」之議,也許可行,頗值得大家重視。
一旦學術課程可以穩定開授,學員的年齡、階級、性別的分佈,便會更加多元,一流師資也會慢慢匯聚。一般大學作專業研究,有一定的規格束縛,社大沒有這些限制,反而有條件可以發展跨領域與大格局的研究。
台灣社會四百年來有多重文化交會,原住民、漢、荷、西、日、美,在台灣都深度介入,再加上近十多年,來自東南亞各國的女性與勞工,共同交織成一個詭異瑰麗,表面均質,底層卻藏著很多有趣矛盾的文化混合體。台灣文化作為一個研究的對象,必然會長出燦爛的花朵。
1970年代後期,唐文標與我時常談起「台灣學」,期待台灣學術界能進行科際整合,研究台灣社會與文化的問題,建立起「台灣學派」(唐叫它作「台北學派」)。解嚴前一兩年,我與台大幾位令人敬重的同事,包括在座的張則周教授,一起籌設「台大教授協會」(後因有人擔心政治勢力打壓,改名叫「台大教授聯誼會)」,我的動機便出於那股期待。當時唐文標已不幸因鼻咽癌辭世,但十年前的願景仍一直留在我心中。可惜該會後來也因擋不住政治勢力的介入而變質。
目前台灣一般大學雖也鼓勵跨領域的研究,但還是分工太細,以技術取向,而缺乏大格局的視野,更沒有探討根本問題的動力。社區大學如果能穩定下來,變成另類的大學,或許真的會建立起「台灣學」,發展出國際矚目的「台灣學派」。
臨稿匆匆,讓我把最後要談的論題:「社區大學與集體意識/唯心主義的辯證關係」,留待日後討論。
|